List of Links
Return to CPRI H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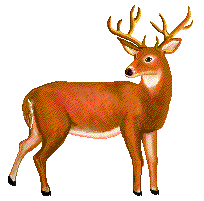
通口篤三
本書(柘植書房新社出版,2,300日元)作者是戰後點燃革命運動火炬的「讀賣(新聞)鬥爭」的領導人,由他來對那些共同戰鬥過的人物寫評傳是很合適的。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書物成千上萬,在日共的正統歷史中,就有《五十年黨史》、《六十年黨史》、《六十五年黨史》、《七十年黨史》等。在日共黨主流以外,有《德田球一》、《神山茂夫》等個人傳記,但卻沒有像《史記》那樣的列傳。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界關於日本革命運動持有的「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日本帝國軍隊式性質。本書可以說是日本第一本革命列傳。
書評作者1947年加入日本共產黨,歷經兩次被開除仍堅持勞工運動,他對於「日本革命史=日本共產黨史=宮本顯志史觀」有深切的體會。除了「日本的列寧」(宮本)以及作為批判、迫害對象的「日本的毛澤東」(德田)、「日本的劉少奇」(志田重男)外,日共正統史觀裡的日本革命運動、勞工運動史上看不見「人」的影子。為了對日本革命的失敗進行歷史性的總結,首先必須不分功成名敗對代表性人物進行綜合評論。本書雖然對個別具體人物的評判不一定正確,但從整體上看,是非常有價值的。
本書列傳的一百人中,有29名日共「職業」黨員,兩名非日共職業革命家(平塚、凡岡秀子)、11名勞工運動組織者(包括日共黨員)、13名文學家、13名藝術家、10名學者、13名新聞界人士等。我雖然比作者年輕15歲,但也直接在書中30多人的領導下工作過,與書中數人也共同工作過。
除了山口武秀(農民運動)、鈴本市藏(國鐵工會與「2.1」總罷工)沒有列入外,結集在列傳中的人物代表了日本「革命黨」第一流的良心、正義感、人格與事業。其中包括日共的德田、野阪參三、志賀義雄(所謂「三巨頭」),金天海、神山茂夫、宮本、褲田里見、黑木重德、志田、椎野悅郎(所謂「再建七幹部」)、春日庄次郎(社會主義革命與構造改革論)、西澤隆二、安齌藏治(「毛澤東派」)等;也有戰後工運巨頭細谷松太、高野實。書中特別提及在日朝鮮人日共幹部(上列)金天海、保阪浩明、車永秀,沖繩人德田、高安重正。至於文學藝術家太宰治、河原宏等,今天的日本人一般只讀其作品,不知道其政治立場。可以說,在戰前天皇制國家、軍國主義統治下奮鬥的日共的道德與良知,在戰後的民主革命鼓舞下一舉開花結果。可悲的是,如書中所列大多數人物一樣,成千上萬的革命者、活動家,都被日共踢散了。
在1947年的日共創立25週年紀念集會上,中野重治作詩《那些人們》歌頌那些沒有正式成為黨員卻為日共犧牲、奮鬥的人們,今天讀起來還令人感動。那是對日本革命、對日本共產黨充滿希望的時代。可惜,中野三年後作為「國際派」被開除;後來雖然在日共六中全會恢復名譽,卻於64年再與神山一同被「永久」開除,此後在日共黨史等文獻中再也見不到其名。「人民之敵」中野去世時,在宮本、藏原支配下的日共,沒有人敢表示悼念。
今天,研究中野的單行本就有247冊,這是任何日本文學、特別是無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學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諾貝爾獲獎者大江健三郎就公開表示:只要日共不改變對中野的態度,他就不會與《赤旗》交往。增山在書中高度評價中野:「我對於文學家中野重治曾經是日共黨員這一事實充滿自豪。我們之間當然有細微的差別,但日共黨員中野的存在,本身就為日共的馬克思主義增添了人性良心的光輝。」除了中野外,野間宏、佐多稻子、安部公房等等,都沒有出現在日共的宮本史觀中。日共的《六十五年黨史》只提及宮本百合子(宮本顯志夫人)的《播州平野》等作品。在宮本40餘年專制性地支配日共期間培植起來的龐大的宮本史觀,將來總會遭到徹底廢棄,但我本人卻是50年日共分裂時宮本的最熱烈支持者。
書中的長谷川浩(原日共政治局委員、工會部部長)晚年表示:有上百萬人脫離了日共。日本研究馬克思、列寧、格拉姆西的泰斗石堂清倫也說有50萬人脫離了日共。總之,這是非常龐大的數目,更令人寒心的是:這些人中,有95%以上的人都不願再提日共了。我自己認識的人當中,只有一位被開除的原日共東京都委員表示如果日共自己批判,願意回日共。實際上,此書的百人中,竟然有60人是脫黨或被開除者。
戰敗後的數年中,日本的民眾為每日的食糧奔波。我這樣48年成為黨專職(職業革命家)的人常常領不到工資、空腹工作。井上光晴的「反黨小說」《不能書寫的一章》就寫實地描述他在長崎縣作為黨專職工作人員的生活之苦。白川晴一(政治局委員)、渡邊四郎、內藤知周(曾是宮本派中心人物之一,當上中央委員後脫黨)等形容自己到70年代還是「赤貧如洗」,更不用說在日朝鮮人黨員們的生活貧困了。車永秀80年以後與我親交,告訴我他48年時在黨本部工作時午餐就是一個乾麵包、一杯白水,但宮本在大家面前獨自吃著白米加炒雞蛋。志賀與野阪也同宮本一樣,而志田、德球則與大家同食,很得人心。增山曾去宮本、志賀家作客,為其豪華住宅驚異。
比起經濟生活的貧困,政治生活的變幻更令人心寒。小松豐吉可能是命運最悲的黨中堅幹部吧!他是東京的三大日共據點工廠組織的領導者,特別在朝鮮戰爭中作為軍事委員會負責人鋒芒畢露。54年被志田委派與椎野、吉田同赴北京(後兩者知道命運不祥拒絕前往),在北京被褲田里見徹底整肅,對黨絕望之餘以酒消愁。歸國後無法工作,被開除後病死在路上,連家人也不認他。我當時所屬的川崎市東芝堀川町組織,在4,500名工人中有380名黨員,是「日本最大」的共產黨支部。當時的支部長K才23歲,他後來與小松命運相同,死在橫濱的街路上,無人認領。黨中央的S也是如此。我自己想來,雖然自己應該負一部份責任,但多數的責任是由於日共黨的政治方針從來沒有為「專職黨員」的生活著想。結果,那些把生命獻給黨的事業的人,或者死心塌地追隨宮本迫害同志,或者被開除出黨又沒法在社會中生存。在日共,宮本的「輝煌」路線下,堆積著過去的同志們的累累屍骨。
(譯者不由得對比托洛茨基臨終前在逃過一次謀殺後對KGB的揭露,指出正是那些犯過錯誤但已經緊密依附黨的機器、沒有能力幹別的工作並習慣於特權位置的人,可以被KGB變成唯命是從的工具,擔當無惡不作的勾當。(註1))
在朝鮮成長、在中國從事活動的安齋庫治(日共中央委員、候補幹部會成員,67年被開除)晚年反省到:「日共在戰前、戰後總是在鬥爭的最困難關頭把朝鮮同志們分派到最危險的地方。這樣做,即使自身沒有意識到,也反映了日共的民族排外主義與皇道思想。」(72頁)
保阪(因與日本人醫生結婚而改成日本姓)在戰爭時畢業於東京大學,在46年1月的日共五大上是三名朝鮮人中央候補委員之一。他在京成電鐵、京濱的東芝、讀賣新聞鬥爭等運動中出盡風頭,在49年時作為東北地方委員會議長指導佔領平警察署以及東神奈川人民電車事件等極端戰術。他在日共六中全會的會議上自我批判時同時也承認「因為自己是朝鮮人始終受到歧視,因而發展成那樣的極端行動」,使整個會場肅靜無聲(74頁)。我與他共事三年,儘管他比我輩份高,也因為不滿他的權力慾而提意見批判過他。
後來讀到他的遺稿集,其中提到他與典代戀愛時,同時戀慕典代的日本人警察調查保阪的出身,在典代面前辱罵他:「朝鮮人也想靠近日本姑娘!」並毆打他。沒想到他受到如此歧視。這使人想到美國白人革命家拒絕與黑人同志握手的情形,這在日本也長期存在。出身沖繩的德田球一又是一例。
德田在故鄉名護市自80年代以來由市政府公報等追頌為「鄉土英雄」、「國際政治家」,由社會黨的戶口市長到保守派的比嘉市長、今天的岸本市長帶動,出資四百萬日元(加上各界捐款共兩千萬日元),花三年時間建成德田紀念碑。自民黨、公明黨、社會黨的市議員們都贊成此項提案,只有共產黨的市議員沒有表態,這是因為日共黨本部的宮本對德田的偏見所致。
70年「沖繩回歸運動」時的日共相關負責人牧瀨恆二曾對增山講過:「德田實際上不認為沖繩是大和(日本)。沖繩共產黨不應從屬於日本共產黨。那樣的話,沖繩人的自主性就喪失了」(250頁)。牧瀨還說:宮本堅持把(沖繩)人民黨組織解散、把沖繩的共產主義運動置於日共的中央集權之下,高安重正(戰後日共的沖繩政策負責人)可能是因為堅持德田的意見而被日共開除的(255 間^。
在日本革命運動史和日共黨史中,最「空白」(或者稱為歪曲)的部份是在朝鮮戰爭時日共的軍事鬥爭準備。
《日共五十年史》把朝鮮戰爭定義為「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發動侵略戰爭」,稱日共的武裝鬥爭是「極左冒險」。《日共六十五年史》稱為「德田派極左冒險主義」,《日共七十年史》又稱為「德田野縣分裂派別的武裝鬥爭路線的破產」。總之,這不是以宮本為正統的日共的行為,而是在中國、蘇聯指使下德田等分裂主義者們的自殺行為。
這是很奇怪的,因為在50年代,斯大林作為國際共產主義(第三共產國際)的絕對領袖,日共不可能違抗。實際上,宮本等在「恢復黨籍」時承認「我們必須開始武裝鬥爭的準備」(220頁),雖然他們可能沒有被安排到直接的這一類工作。但是,我們知道,早稻田大學的日共支部負責人由井誓在恢復黨籍後,作為懲罰,被派到東京最艱難的奧多摩的小河內工作隊,準備建立毛澤東那樣的山村政府。
50年秋天,九州地方委員會山本議長因為持有麻藥而被逮捕,被新聞大肆報導為日共地下武裝準備的證明。我們黨員一直聽信正統黨史,以為那是日本政府的謊言,但後來知道那是事實。
按照本書的材料,在山村建立武裝鬥爭據點是日共四次會議(51年2月)軍事方針「志田構想」的一部份,由被麥克阿瑟肅清出日本社會的黨員等兩千五百多人組成五十五個中核自衛隊與獨立遊擊隊(213頁)。據小松豐吉證實,他看到「從日本偷渡到中國的青年組成『日本人民軍』在沿海接受登陸作戰訓練」(215頁)。與此相關的是在與中國往返中活躍的「人民艦隊」組織者永山正昭以及為了「特殊財政」(搶劫資金)組成的「卡車部隊」隊長大村英之助。大村曾是日共的文化部長,頗有文才,是植村申午郎(經團連會長)親戚。但他被任命為「卡車部隊」隊長,成為日共武裝鬥爭失敗的替罪羊,被日共在六次會議上以「貪污無恥」罪趕出日共並因此被投入監獄。我們長年以來都認為那傢伙臭名昭著、罪有應得。而實際上,「特殊財政」的部份資金被志田重男貪污,在東京的神樂縣高級餐廳揮霍浪費。此事被佐和慶太郎揭露後(235頁),宮本只好開除了他的這個親信。
誰也不知道因「貪污無恥」罪入獄的政治犯大村的命運。還有小松豐吉,姐牙仁郎等成為「廢物」在新宿開小麵館為生的人,他們曾經忠實地執行黨中央的政策迫害他人,最後又被黨開除,無法回歸社會,他們的心靈會安寧嗎?與那些被敬貢的「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之墓」、被合祀在「日本共產黨常任活動家之墓」(東京都八王子市上川靈園)的幸運左翼人士相比,誰去悼念那成千上萬的為日本革命事業奮鬥犧牲、經歷悲壯人生的「無名戰士們」呢?
(趙京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0年10月23--12月4日號)
註1:李時譯《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斯大林謀害我的生命》,刊香港《十月評論》2000年第4期。
十月評論 2000年第5/6期